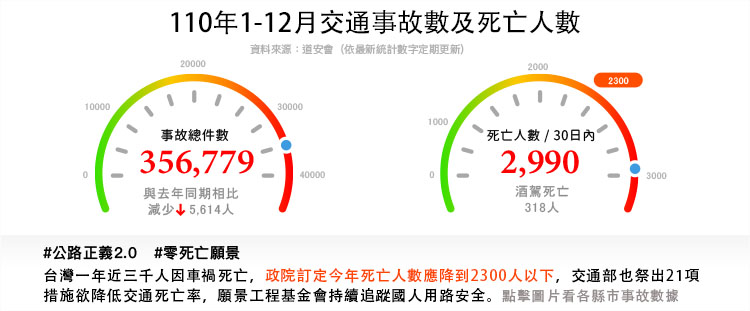解決營造業缺工 學者建議提升職人地位、導入自動化
台灣缺工警報響不停,專家直言長遠之計是改善勞動條件、推動科技導入工程,並強化專業人才培育,才能紓解困境。台灣區綜合營造業公會理事長陳煌銘則直接點名四百多億就業安定基金,政府要用這筆錢開設技職訓練班,而不是拿去裝潢辦公室或開演唱會;也要強化技職教育,培養本土技術人員。...

阿鴻把工地變舞台 女兒大讚好帥
「工地是我的舞台,水泥、磚牆與『西阿給(粉光)』是用雙手勾勒的藝術。」四十五歲的鄭志鴻國中畢業,臉書「泥作阿鴻」是他分享水泥工日常的粉絲專頁,有廿萬人追蹤,透過文章、出書、演講讓更多人看到做「土水(台語,水泥工)」的職人價值。...